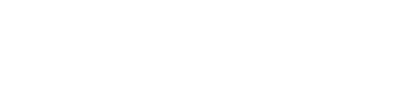談軟件發(fā)明專利侵權(quán)糾紛案件的技術(shù)事實(shí)查明
案情介紹
北京搜狗科技發(fā)展有限公司(以下簡(jiǎn)稱“搜狗公司”)是名為“一種用戶詞參與智能組詞輸入的方法及一種輸入法系統(tǒng)”專利的權(quán)利人。搜狗公司認(rèn)為,“OnePlus2”手機(jī)預(yù)裝的Android版百度輸入法系統(tǒng)包含了建立用戶二元庫的方法,百度輸入法能夠在用戶輸入文字的過程中記錄用戶對(duì)句子的輸入和對(duì)上屏詞的選擇操作。其中,百度輸入法“隱式自造詞”的技術(shù)方案,落入了搜狗公司涉案專利權(quán)的保護(hù)范圍,侵害了其公司的發(fā)明專利權(quán)。百度在線網(wǎng)絡(luò)技術(shù)(北京)有限公司(以下簡(jiǎn)稱“百度在線公司”)、北京百度網(wǎng)訊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簡(jiǎn)稱“百度網(wǎng)訊公司”)共同制作了百度輸入法,百度在線公司在百度軟件中心、百度輸入法官網(wǎng)、APP Store、各類Android應(yīng)用市場(chǎng)、各類軟件下載網(wǎng)站發(fā)布和對(duì)外提供Android版百度輸入法、iOS版百度輸入法和PC版百度輸入法等,供公眾下載,用戶注冊(cè)協(xié)議顯示該協(xié)議由百度網(wǎng)訊公司與注冊(cè)用戶簽訂。此外,兩百度公司將百度輸入法提供給手機(jī)廠商讓其預(yù)裝在所生產(chǎn)的手機(jī)中。上海天熙貿(mào)易有限公司(以下簡(jiǎn)稱“天熙公司”)許諾銷售、銷售預(yù)裝有百度輸入法的“OnePlus2”手機(jī)。
據(jù)此,搜狗公司將百度在線公司、百度網(wǎng)訊公司及天熙公司訴至上海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法院,請(qǐng)求法院判令百度在線公司、百度網(wǎng)訊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涉案發(fā)明專利權(quán)的行為;判令天熙公司立即停止許諾銷售、銷售預(yù)裝有侵害涉案專利權(quán)的百度輸入法的手機(jī);判令兩百度公司賠償搜狗公司包括為制止侵權(quán)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在內(nèi)的經(jīng)濟(jì)損失1000萬元。其中,5萬元由天熙公司連帶賠償;本案訴訟費(fèi)用由三被告共同承擔(dān)。
被告百度在線公司、百度網(wǎng)訊公司辯稱,百度輸入法在技術(shù)上不記錄詞與詞之間的關(guān)聯(lián)關(guān)系,與搜狗公司的專利技術(shù)并不相同,且百度輸入法系免費(fèi)軟件,不會(huì)影響搜狗公司的損失或者兩百度公司的獲利,搜狗公司的索賠沒有事實(shí)依據(jù)。被告天熙公司辯稱,無法證明被控侵權(quán)的“OnePlus2”手機(jī)來自于天熙公司。
上海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法院經(jīng)審理認(rèn)為,涉案專利的二元詞對(duì)需要參與計(jì)算概率,因此,涉案專利二元詞對(duì)的技術(shù)特征不僅記錄“相鄰的兩個(gè)詞”,還記錄“該兩個(gè)詞之間的相鄰關(guān)系”。相比較被控侵權(quán)軟件與涉案專利的二元詞對(duì)技術(shù)特征,二者相同之處在于均記錄了相鄰輸入的詞,不同之處在于被控侵權(quán)軟件未區(qū)分形成同一自造詞的不同組合,即未記錄相鄰詞的相鄰關(guān)系。此外,根據(jù)涉案專利說明書、涉案專利無效宣告請(qǐng)求審查決定,可知“詞頻”與“概率”之間存在區(qū)別和聯(lián)系。詞頻是用戶輸入某特定詞的頻次。涉案專利中的概率指用戶輸入某相鄰詞對(duì)在用戶輸入的所有相鄰詞對(duì)中出現(xiàn)的可能性。二者相同之處在于:均受用戶輸入該特定詞次數(shù)的影響,但均不簡(jiǎn)單等于用戶輸入的次數(shù)。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:概率T(A,B)/(SUMBI)受用戶輸入二元詞對(duì)的總次數(shù)(SUMBI)影響,而詞頻不受用戶輸入二元詞對(duì)的總次數(shù)(SUMBI)影響。經(jīng)過對(duì)被控侵權(quán)軟件進(jìn)行測(cè)試并勘驗(yàn)源程序,被控侵權(quán)軟件根據(jù)用戶輸入自造詞的總次數(shù)賦予用戶自造詞相應(yīng)的詞頻信息,但未統(tǒng)計(jì)用戶自造詞占所有用戶所有自造詞的概率。涉案專利權(quán)利要求書及相關(guān)專利審查文檔已明確區(qū)分“詞頻”和“概率”的不同含義。因此,在專利侵權(quán)判斷中,應(yīng)將二者直接認(rèn)定為不同的技術(shù)特征,而不再考慮二者是否構(gòu)成等同。據(jù)此,被控侵權(quán)軟件與涉案發(fā)明專利權(quán)利要求構(gòu)成不同,沒有落入涉案專利權(quán)利要求的保護(hù)范圍。
綜上,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》第十一條第一款、第五十九條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關(guān)于審理侵犯專利權(quán)糾紛案件應(yīng)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第七條之規(guī)定,上海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法院作出一審判決,駁回原告搜狗公司的全部訴訟請(qǐng)求。
一審判決后,原告搜狗公司不服,向上海市高級(jí)人民法院提起上訴。上海高院經(jīng)審理認(rèn)為,一審判決認(rèn)定事實(shí)清楚、適用法律正確、審判程序合法,所作判決并無不當(dāng)。遂于2020年3月30日作出終審判決,駁回上訴,維持原判。
舉證責(zé)任的分配
(一)專利法舉證責(zé)任規(guī)定的歷史變化
專利侵權(quán)案件的舉證責(zé)任規(guī)定與民事侵權(quán)案件在原則上無異,即根據(jù)“誰主張、誰舉證”的原則進(jìn)行責(zé)任分配。權(quán)利人主張被控侵權(quán)產(chǎn)品侵犯其專利權(quán)的,應(yīng)當(dāng)承擔(dān)舉證責(zé)任,證明被控侵權(quán)產(chǎn)品落入其專利權(quán)的保護(hù)范圍。若不能證明的,則權(quán)利人依法承擔(dān)敗訴的法律后果。
但例外的是,對(duì)于新產(chǎn)品制造方法的發(fā)明專利,采用舉證責(zé)任倒置的規(guī)則。所謂新產(chǎn)品是指專利申請(qǐng)日前不被國內(nèi)外公眾所知的、由涉案專利方法直接獲得的產(chǎn)品。然而,實(shí)踐中發(fā)現(xiàn),由于法律沒有明確規(guī)定非新產(chǎn)品制造方法的專利侵權(quán)訴訟應(yīng)該如何分配舉證責(zé)任,造成了審判標(biāo)準(zhǔn)混亂,容易導(dǎo)致同案不同判,影響司法權(quán)威。在2013年中國法院50件典型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案例中,一起侵害發(fā)明專利權(quán)糾紛案件的判決指出,在專利權(quán)人能夠證明被訴侵權(quán)人制造了同樣產(chǎn)品,經(jīng)合理努力仍無法證明被訴侵權(quán)人確實(shí)使用了該專利方法,根據(jù)案件具體情況,結(jié)合已知事實(shí)及日常生活經(jīng)驗(yàn),能夠認(rèn)定該同樣產(chǎn)品經(jīng)由專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很大的,人民法院可以將舉證責(zé)任分配給被訴侵權(quán)人,不再要求專利權(quán)人提供進(jìn)一步的證據(jù),而由被訴侵權(quán)人提供其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的證據(jù)。
最終,該判決理念在2020年通過并實(shí)施的《最高人民法院關(guān)于知識(shí)產(chǎn)權(quán)民事訴訟證據(jù)的若干規(guī)定》以成文法的形式固定下來。其中,第三條規(guī)定,專利方法制造的產(chǎn)品不屬于新產(chǎn)品的,侵害專利權(quán)糾紛的原告應(yīng)當(dāng)舉證證明下列事實(shí):(一)被告制造的產(chǎn)品與使用專利方法制造的產(chǎn)品屬于相同產(chǎn)品;(二)被告制造的產(chǎn)品經(jīng)由專利方法制造的可能性較大;(三)原告為證明被告使用了專利方法盡到合理努力。原告完成前款舉證后,人民法院可以要求被告舉證證明其產(chǎn)品制造方法不同于專利方法。該條基本與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論述相同,即包括相同產(chǎn)品、利用專利制造的可能性、舉證的合理努力。權(quán)利人需滿足以上三個(gè)要件,舉證責(zé)任方才轉(zhuǎn)移給被控侵權(quán)人。
(二)軟件發(fā)明專利侵權(quán)案件的舉證責(zé)任分配
軟件發(fā)明專利本質(zhì)上屬于方法專利,與機(jī)械等其他類型的專利不同,有其特殊性。軟件發(fā)明專利保護(hù)的是其代碼而非外在的技術(shù)效果,權(quán)利人取得被控侵權(quán)產(chǎn)品后無法像其他產(chǎn)品一樣通過拆解來研究,故在舉證責(zé)任的分配上有所不同。
在軟件發(fā)明專利侵權(quán)案件中,不宜給權(quán)利人分配過多的舉證責(zé)任,但又不能免除其舉證責(zé)任,而是要在權(quán)利人與被控侵權(quán)人之間不斷轉(zhuǎn)移。因權(quán)利人無法掌握軟件的源代碼,故僅需先舉證被控侵權(quán)軟件具備了涉案專利限定的全部功能、侵權(quán)的可能性較大;之后,由被控侵權(quán)人舉證證明其產(chǎn)品雖然實(shí)現(xiàn)了同樣的技術(shù)功能和效果,但其采用了有別于涉案專利的技術(shù)方案。此時(shí),若被控侵權(quán)人不舉證或無法證明該待證事實(shí)的,法院則應(yīng)依法判決認(rèn)定侵權(quán);若被控侵權(quán)人舉證證明其采用的方法與涉案專利不同,舉證責(zé)任則再次轉(zhuǎn)移給權(quán)利人,由權(quán)利人舉證證明被控侵權(quán)人的主張不成立;若權(quán)利人能夠舉證證明上述待證事實(shí),則舉證責(zé)任再次轉(zhuǎn)移給被控侵權(quán)人;若權(quán)利人不舉證或無法證明該待證事實(shí),則法院依法判決認(rèn)定不侵權(quán)。
本案中,法院在審理時(shí)基本依照了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精神。搜狗公司提出相關(guān)實(shí)驗(yàn)以證明百度輸入法軟件在組詞過程中存儲(chǔ)并調(diào)用了二元詞對(duì),搜狗公司作為權(quán)利人已經(jīng)承擔(dān)了初步的舉證責(zé)任。此時(shí)舉證責(zé)任轉(zhuǎn)移至兩百度公司,由兩百度公司進(jìn)行一系列反證實(shí)驗(yàn),證明其不存在具有相鄰關(guān)系的用戶字詞對(duì),也未統(tǒng)計(jì)并存儲(chǔ)用戶字詞對(duì)在用戶輸入時(shí)相鄰出現(xiàn)的概率。本案中,兩百度公司還向法院提交了被控百度輸入法軟件源代碼進(jìn)行勘驗(yàn)。因此,在搜狗公司進(jìn)行相關(guān)實(shí)驗(yàn)后,兩百度公司已經(jīng)盡到了相應(yīng)的舉證責(zé)任。此時(shí),舉證責(zé)任再次轉(zhuǎn)移給權(quán)利人。
在整個(gè)舉證過程中,法官處于居間的位置,引導(dǎo)當(dāng)事人進(jìn)行舉證,以便查清事實(shí)、保障案件的審理有序進(jìn)行。舉證責(zé)任并不是在法官作出侵權(quán)與否的假定或內(nèi)心印證下進(jìn)行分配,而是體現(xiàn)了“以事實(shí)為依據(jù)、以法律為準(zhǔn)繩”的依法裁判原則。誠然,在專利侵權(quán)訴訟中,當(dāng)事人在代理人的幫助下對(duì)于應(yīng)當(dāng)如何證明侵權(quán)或不侵權(quán)有專業(yè)性的把握,將舉證責(zé)任根據(jù)舉證情況分配給雙方當(dāng)事人不僅能夠減輕法院審理的壓力,還有利于在舉證責(zé)任的轉(zhuǎn)移中最大程度還原事實(shí)。
專利保護(hù)范圍的確定
專利侵權(quán)即被控侵權(quán)產(chǎn)品的技術(shù)特征落入了權(quán)利人享有的專利權(quán)的保護(hù)范圍。在侵害發(fā)明專利權(quán)與侵害實(shí)用新型專利權(quán)的案件中,存在相同侵權(quán)和等同侵權(quán)兩種形式。相同侵權(quán)即被控侵權(quán)產(chǎn)品技術(shù)特征與專利權(quán)權(quán)利要求中的技術(shù)特征相同;等同侵權(quán)即被控侵權(quán)產(chǎn)品的技術(shù)特征與專利權(quán)權(quán)利要求中的技術(shù)特征雖不相同,但并不具有實(shí)質(zhì)性差異。無論是相同侵權(quán)還是等同侵權(quán),判斷侵權(quán)與否的第一步都是確定專利權(quán)的保護(hù)范圍。
(一)專利公開文本
法院在確定發(fā)明專利和實(shí)用新型專利保護(hù)范圍時(shí)依據(jù)的專利公開文本一般為權(quán)利要求書、說明書、附圖,確定外觀設(shè)計(jì)專利保護(hù)范圍時(shí)依據(jù)的則為照片、簡(jiǎn)要說明等。通常而言,一項(xiàng)技術(shù)方案由若干技術(shù)特征組成,法院在分析技術(shù)特征時(shí),一般從整體技術(shù)方案的角度分析,既考慮記載在技術(shù)特征字面上的含義,還關(guān)注技術(shù)特征之間的內(nèi)在聯(lián)系。最高人民法院在審理某電器公司、某生物科技公司侵害實(shí)用新型專利權(quán)糾紛案件時(shí)同樣指出,專利技術(shù)特征的理解應(yīng)當(dāng)基于該專利要解決的技術(shù)問題,結(jié)合該技術(shù)特征所表達(dá)的技術(shù)手段、在整體技術(shù)方案中與其他技術(shù)特征之間的配合關(guān)系、所發(fā)揮的技術(shù)功能和效果來進(jìn)行。
本案中,根據(jù)涉案專利具體實(shí)施方式[0069]段記載,“二元詞對(duì)是指用戶在輸入過程中具有相鄰關(guān)系的用戶字詞對(duì)”。[0058]段記載,“所述用戶二元庫通過記錄用戶對(duì)句子的輸入和對(duì)上屏詞的選擇,記錄或更新同一句子中兩個(gè)相鄰輸入的用戶詞之間的用戶二元關(guān)系”。涉案專利說明書[0096]段記載“二元詞對(duì)A-B的二元概率為T(A,B)/SUMBI,其中,T(A,B)為A-B二元詞對(duì)在用戶輸入時(shí)出現(xiàn)的總次數(shù),SUMBI為所有用戶二元詞對(duì)的總次數(shù),即所有T(,)的總和。增強(qiáng)A-B的二元概率就是T’(A,B)=T(A,B)+1,增強(qiáng)后的A-B二元概率即為T’(A,B)/(SUMBI+1)”。
可見,涉案專利的二元詞對(duì)需要參與計(jì)算概率。因此,涉案專利二元詞對(duì)的技術(shù)特征不僅記錄“相鄰的兩個(gè)詞”,還記錄“該兩個(gè)詞之間的相鄰關(guān)系”。通過測(cè)試可以發(fā)現(xiàn),被控侵權(quán)的百度輸入法軟件與涉案專利的二元詞對(duì)技術(shù)特征,二者相同之處在于:均記錄了相鄰輸入的詞;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:被控侵權(quán)的百度輸入法未區(qū)分形成同一自造詞的不同組合,即未記錄相鄰詞的相鄰關(guān)系。故兩百度公司的輸入法與搜狗公司的輸入法在技術(shù)方案等方面存在區(qū)別,此時(shí)排除了相同侵權(quán)。
(二)專利審查文檔
根據(jù)《最高人民法院關(guān)于審理侵犯專利權(quán)糾紛案件應(yīng)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(二)》第六條規(guī)定,專利審查檔案也可作為確定保護(hù)范圍的依據(jù),這也是專利法上“禁止反言”原則的體現(xiàn)。若允許權(quán)利人在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中有不一致的表述,將會(huì)導(dǎo)致公有領(lǐng)域邊界的模糊,造成現(xiàn)有技術(shù)使用產(chǎn)生不安定性。
本案中,根據(jù)專利復(fù)審委員會(huì)在涉案專利《無效宣告請(qǐng)求審查決定》中的記載,“本領(lǐng)域技術(shù)人員能夠明確,用戶詞頻的調(diào)整與對(duì)應(yīng)的用戶字詞對(duì)相鄰出現(xiàn)的概率調(diào)整是相應(yīng)的。本領(lǐng)域技術(shù)人員能夠根據(jù)具體的需求設(shè)計(jì)調(diào)整方式。例如,用戶詞頻調(diào)高,對(duì)應(yīng)的用戶詞對(duì)相鄰出現(xiàn)的概率也調(diào)高處理。因此,上述特征能夠得到說明書支持”“權(quán)利要求1中的用戶詞對(duì)相鄰出現(xiàn)的概率也可稱為多元概率,是指多元信息的使用概率。基于本專利的整體發(fā)明構(gòu)思來看,權(quán)利要求1中的用戶字詞對(duì)相鄰出現(xiàn)的概率是以用戶各次的歷史輸入作為統(tǒng)計(jì)范疇的,統(tǒng)計(jì)的是在用戶輸入過程中目標(biāo)多元組作為一個(gè)整體出現(xiàn)的概率。其數(shù)學(xué)含義是,針對(duì)用戶輸入情況下,以用戶輸入的所有相鄰情況為統(tǒng)計(jì)基數(shù)(分母),以用戶輸入過當(dāng)前多元詞對(duì)的次數(shù)為分子,所計(jì)算得到的概率。也就是說,權(quán)利要求1中的概率是指一個(gè)多元組作為一個(gè)整體出現(xiàn)的概率,它是基于統(tǒng)計(jì)得出的,是對(duì)整體性的估算”“在權(quán)利要求1的用戶多元庫中為用戶字詞對(duì)保存的概率則是用戶輸入時(shí)相鄰出現(xiàn)的概率,即用戶字詞對(duì)在用戶輸入時(shí)相鄰出現(xiàn)的可能性。也就是說,這個(gè)概率是相對(duì)于用戶所有可能輸入的相鄰字詞對(duì)而言的,其表示的是該用戶字詞對(duì)在用戶所有可能輸入的相鄰字詞對(duì)中出現(xiàn)的可能性”。
綜上所述,本案通過舉證責(zé)任的不斷轉(zhuǎn)移,使得法院在當(dāng)事人雙方積極舉證的情況下查清了有關(guān)事實(shí)。法院依據(jù)專利文本、專利審查文檔等確定涉案專利的保護(hù)范圍,將涉案專利產(chǎn)品與被控侵權(quán)產(chǎn)品進(jìn)行比對(duì),發(fā)現(xiàn)二者存在不同,最終認(rèn)定兩百度公司不構(gòu)成侵權(quán)。